扳道工事案的法理简析——法的效益与秩序冲突分析
Posted on 2016-07-13 by maxvisadmin
事案简述——扳道工事案
在一片群山的脚下,有一座小小的房屋,那是扳道工的工房。在房屋的旁边,一条蜿蜒的铁路分为并行的两支,其中一支旧铁道已经废弃,另一支新铁道在正常使用。它们都弯曲地伸向群山怀抱中的村庄,经过村庄向更远方伸去。
这是一个宁静的黄昏,夕阳把余晖抹在林梢和山峦之上。因为今天是中秋节,在山坡上劳作一天的农民要赶回已冒起袅袅炊烟的村庄了,他们选择走便捷的但在正常使用的轨道,他们知道这行为不仅违法,而且危险。但是家人已经迫切地等待他们回家团聚。
在另一条废弃的铁轨上,一个衣着褴褛的人也向村庄的方向走去。他从一个监狱中逃出,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他向扳道工乞讨来的水和食物不足以解决他的饥渴。他想到村庄去弄点好吃的。看到升起的炊烟,他似乎闻到了热腾腾的饭菜和喷鼻的香味。
指示乞讨者沿着正确的道路行走之后,扳道工悄悄地拨通了报警电话。这个人与发到工房的通缉布告上的囚犯肖象完全一样。
刚刚放下电话,铁路内线电话就响了。一个紧急的通知说,马上有一列火车要经过道口。最近临时加开的列车有点多。当他走出房门,似乎已经听到列车的汽笛。同时,他也看到了那群走远的人们已经变小的身影:在废弃的铁道上走着那个人-一个逃犯,在正常使用的铁道上走着七个农民。列车司机也已经看到这一切,拉下来紧急刹车,但是列车仍然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冲向道口。
站在道口的,就是那位扳道工。他应该怎样扳道呢?

该事案是一个思想实验,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不同方面对扳道工的选择甚至是扳道工掌握的自由裁量权进行讨论。而从法律的价值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该事案最重要的体现了一个价值选择的困境,显示了不同价值之间的尖锐冲突。扳道工就好比一个国家的法律或政策的制定者,有时候需要在这两个方面进行选择:是为了促进社会的整体福利而牺牲部分人的利益,还是为了公平地对待部分人而在某种程度上牺牲社会的一些整体福利。而这个问题,集中体现了法的价值一直存在的冲突与调和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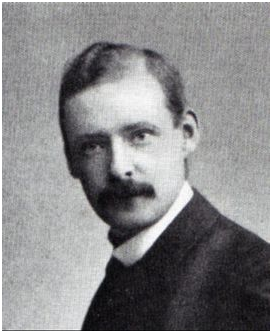
法的价值,是指法律基于其存在、状态或属性而具有的对人们的有益作用或积极意义。人们有时会把法律的价值与法律的属性等同起来。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就认为,法律的价值有三个方面:安定性、正义和和目的性。也有认为法的价值可以分为两个方面:1、法的形式性价值,即法律在形式、程序方面具有什么价值;2、法的实质性价值,即法律在规范内容方面促进哪些价值。形式性价值和实质性价值的区别是相对的,它们之所以是价值,在于它们都是一个社会所追求的,都是社会价值。
在逻辑层面上,介于具体价值与最终价值之间的是法的基本价值。法律基本价值可以归纳三个方面:秩序、效益、正义。法的基本价值具有多元性、相通性、冲突性,它们既相辅相成,又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不同价值有相通和兼容之处,也有冲突的可能。对于调和法的价值冲突,一般主张采用适当的态度,适用包括统筹兼顾原则、恪守底线原则、与时俱进原则、审议民主原则、均衡宪政原则等原则,结合现实的情况及局面进行解决,这便要求法律的制定者及权力机关对于法的价值原则有非常深厚的认识。而本文中就此事案分析的法的价值冲突,也主要是针对法的基本价值冲突方面进行探讨研究。
本事案中,如果将扳道工置于一个国家的法律或政策的制定者,将火车导向往哪一条轨道,则体现了制定者在制定法律或政策中必须要面对的价值冲突及取向问题。无论火车冲向哪一条轨道,终将会有人因为扳道工的决定而失去生命,都不能称之为是“正义”的行为。问题的分歧在于,是否应牺牲本身便有罪行但走在规定的轨道中的逃犯,还是应牺牲违反了规定走在使用中的铁轨上但有七个生命的农民!牺牲农民,可以将此次事故牺牲的生命数量降到最低,但却违反了已经制定实施的规定。牺牲逃犯,维护了已经制定实施的规定,但却让此次事故中牺牲的生命数量达到七名,而且,这位逃犯可能本身就是犯有应受死刑刑罚的罪名。

用上面段落陈述到的法的价值内容,无论哪条轨道都不能称之为“正义”的行为,故不涉及到法的正义价值。选择哪条轨道,就是当法的秩序价值与效益价值发生冲突时,应当如何选择。就本案扳道工所遇到的情况,笔者是坚定不移地选择火车向正常的轨道上行驶的。已经废弃的轨道与正常使用的轨道,作为当地的村民,对于两条轨道的使用情况是十分明确清晰的,当天为了尽早到达家里,选择了危险且违法但是便捷的道路,即走上了使用中的轨道。这一行为放大到现实生活中,则反映了一部分群体为了自身的便利,以违反法律,牺牲既定规则为代价,达到自身的目的。而作为逃犯,他所行走的轨道按法律规定本身便是废弃不用的,理论上是不会有火车经过这条轨道。如果选择将火车引向废弃的轨道,放大到现实中便是为了追求某一特定事故中损失的最低化,而随意更改甚至是破环已经制定实施的法律法规。显然这一做法从长远角度看是达不到立法者当初的立法目的,更达不到决策者所要追求的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法律的制定,是立法者为了其所处的整个社会或国家长期发展所制定的规则法则。法律的公平性是其能长久有效实施的基础,良好完善的法律是为整个社会服务,而非为某一群体或利益集团服务。当然社会效益也应该是立法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一部法律的实施导致了社会某一或全方面的生产力等效率明显低于之前,且这种低下是长期或永久性的,则这部法律是不适合当今社会的,是不应该继续实施的。但今天根据上述事案所讨论的,并不是长期或永久性会出现的情况,是某一次无法预料的事故,具有偶然性、暂时性。因此,在这个事故中即使是牺牲了数量相对多的成本,但却保护了法律的权威及尊严。我们可以清楚地认知,法律规定禁止在使用的轨道上行走,是对整个周边居民都起到保护作用的。将其放至现实中,便是意指那些对整个社会秩序都有益的法律,而且是能够长期有效提高社会效益的。如果仅仅是因为一次事故的发生,便随意违反法律的规定,这不仅会打击守法者的积极性,更会为那些旁观的、一直对违法跃跃欲试的群体给予动力,久而久之,便会形成“法不责众”“有法不依”的观念。当今中国的法治环境,便十分符合这两点特色。而且从长远角度看,如果每次价值冲突都是以社会效益为先,那么“效益”的大小是如何衡量?如果在废弃的轨道上的不是逃犯而是亿万富翁,是以生命数量衡量还是以生命创造财富衡量?显然这是一个太过于依赖人的意志的自由裁量的过程,与立法者制定法律以及建立法治社会的初衷背道而驰。

或许有人提出,逃犯可能本身就犯有死罪,早晚是要失去生命,何不用以牺牲其生命来挽救七个农民?这种做法的弊端,还是上节提到的问题。逃犯犯有死罪,则会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相应的程序及惩罚手段,除此之外,他的生命仍应受到尊重。在没有得到逃犯同意的前提下,谁也没有权力任意剥夺他的生命,否则,社会便会私刑四起,这与犯了死罪的逃犯有何区别?
法律已经制定,便应不可随意更改地执行下去,即使认为该法律的制定及实施有错误或严重滞后,也应按照其他法律制定的程序进行变更或修改,而非某个体能够随意修改,不管该个体的地位或意图是什么样的。因为一旦打开先河,则会像细小的蚁穴一样,最终会将法治的长堤毁于一旦!

